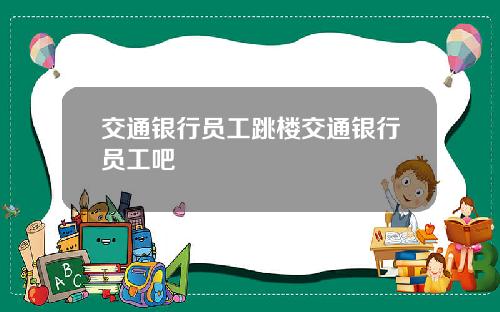每当想起他们就觉得很温暖
作者:小智 发布时间:2024-12-11 栏目: 理财课堂 0浏览
文 刘明辉 图 任署林
还有几天,教师节就要到了。
每个人的求学路上,总会遇到几位想起来就觉得温暖的老师。他们,似一束光,照亮我们的惆怅、困顿和迷思。即便许多年过去,只要想起他们,内心涌起的都是满满的感动,就像大连出版社社长刘明辉笔下的这些老师。
你还在长身体
今后不许挑那么重的担子
1964年5月,我出生在汨罗江边的一个叫流花洲的村子。汨罗江是诗家的圣地,因屈原而出名。千百年来,刘伶、嵇康、李白、苏东坡、秋瑾、闻一多等历代文人墨客都曾为汨罗江吟唱。
我是1970年3月上的小学。最开始,我上的是我们生产小队(自然村)的小学。那时小学条件很差,没有教室,上课地点是生产队会计家的堂屋(这个堂屋白天是我们的教室,晚上是扫盲班的教室,也是生产队的会议室)。没有座椅,坐的是泥砖。没有课桌,泥砖上搭上一块长木板,就是课桌。没有作业本、笔记本,每人一块石板,写完可以擦,擦完再写。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总共不到20人,都在一个班上课。语文、算术、体育、音乐,所有课程都是一个叫刘皇祖的民办老师教。刘老师既是任课老师,也是班主任、校长。通常是某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另外两个年级的学生做作业,但体育课和音乐课是三个年级一起上。体育课基本上是抢皮球,音乐课基本上是听刘老师拉二胡。刘老师二胡拉得好,他一上音乐课,村里的妇女都放下手上的活计,凑在一起听。刘老师读的书多,会讲“三国”里的故事。刘老师的字写得好,过年时,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要找他写对联。谁家添农具了,会找他在农具上写个字。谁家闹矛盾了,会找刘老师去做调解。我们生产队长、会计和民兵连长都对刘老师十分敬重。村里有事出现争议都会说,要不我们问问刘老师怎么说。那时的我,总幻想有一天我会成为刘老师,我发誓要好好读书,要做一个像刘老师那样有知识的人。
一年后,我们生产队的小学撤销了,我们三个年级的学生一起转到大队(现在的行政村)的“汨东完小”。到新学校后,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姓“左”,却是个“右派”。
语文老师近六十岁,感觉她先生年龄更大些,走路有些站不稳的感觉。听说他们夫妇俩都是大学生,是作为“右派”到农村接受无产阶级再教育而下放到我们村的。村里看他们年龄大,做不了农活,就照顾进了村小学。转学后第二天,左老师就给我改了个名字。我的原名叫刘建辉,同班还有一个刘建辉,他父亲是转业军人,任大队民兵营长,他不同意自己儿子改名,那就只能是我改名。左老师说,明辉明辉,日月生辉,明辉这个名字响亮、上口、好记,就这样我就成了刘明辉。
左老师说话声音很轻,她的手指从来没往学生的方向指过,更没有让哪位同学罚过站。但是很奇怪,她的食指很有魔力,无论教室里多闹腾,只要左老师的食指往嘴上一贴,教室里马上就会鸦雀无声。左老师经常做家访,有一次我偷听到了她和母亲的谈话,她本来很细的声音被她压低后,我还是听到了。我妈说,建伢子聪明不?左老师说,刘明辉很聪明,但在孩子面前只能表扬他勤奋,不能表扬他聪明。另外,孩子已经二年级了,不能再叫小名,要叫大名,要培养孩子从小自尊、自爱。
在汨东完小的四年半时间里,几乎是在学工、学农、学军以及各种运动中度过的。我是班里的劳动委员,尽管个头我最小,但挑土我最多,一般重活难活抢着干,老师见了都表扬我,让我再接再厉。只有左老师不时露出别人难以察觉的表情,我能看到的是担心。有一次,她把我叫到她屋里跟我说,你想多干活的态度是值得鼓励的,但你这么干活我要批评你,你还在长身体,今后绝对不许挑那么重的担子,你要在班里带头少干重活。
挽救未来的唯一希望
就是改变现在
1977年秋季,我进入高中。1979年公社中学撤销高中部,高中学生需到县城的第七中学上学(现汨罗市第二中学)。到县城中学念书,我不但不能再帮家里干活,还要在学校住宿,又要多花一大笔钱。县里高中开学快一个月了,我还在家干农活。
“想读大学?我们流花洲没有那个祖宗!”说这话的是我的一个同宗亲戚。县城高中的老师来到家里,劝我父母让我继续读下去,说我学习刻苦,一定能考上大学。老师向我父母承诺我的学费和住宿费他们包了,只要家里每个月拿45斤大米就行(那时候缺油水,一顿一斤大米都不够吃)。
初中时的班主任黄荣华老师也来做工作了,黄老师的一句话让我永生难忘——“挽救未来的唯一希望就是改变现在”。最后,我上学了(家里拿不出大米,用100斤红薯顶的;学费和住宿费总额多少不知道,几位老师要分摊,最后校长和教导主任商量给免了),但我的弟弟和妹妹却辍学回家了,这也成为我一生永远的痛!
在县城高中,我从普通班开始,连跳几个班,最后进入尖子班。高考临近,班里学生除了我,都订了一套高考复习资料,一套几块钱,但是我掏不出这个钱。书发下来那天,我借故离开教室。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难堪和难过,在操场上走了几圈。当我返回教室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书桌上也有和其他同学一模一样的一套复习资料,我跟班主任政治老师刘国伦说:“我没有买这套书。”刘老师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知道,这是刘老师第三次给我买东西了:刘老师让我帮他油印复习资料时,给我买过面包;冬天看我光着脚,给我买过袜子。
拿着这套来之不易的高考复习资料,我就连周末在家里帮厨拉风箱时也在看。那本书挺厚,又包着书皮,那天,正在做饭的母亲误会了,她以为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我还在看闲书,“我让你再看”,她一把从我手里夺过书,直接扔到熊熊的灶火里,我奋不顾身地从灶火里把书又给救了回来。今天想来,我救回的不只是书,也救回了老师对我的期望,更救回了我的今天。
1980年6月高考那几天,中午是在黄老师家吃饭休息的,戴的手表是黄老师从手上摘下来送我的。我们那年英语考试总分只有30分。作为英语老师的黄老师非常明智地在高考前一个月让我放弃复习英语,将精力全用于主科。很幸运,尽管我的英语只考了9分,但我仍以全校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因为身高的限制,我没能考上最想去的北京师范大学(师范生,国家补贴多,能帮家里省些钱)。湖南财经学院录取了我。流花洲村终于出了一位大学生,村邻亲戚都要我家请客。
请客那天,我从半晌午就在江边等着接老师,望眼欲穿。到下午两点的时候,江面上终于来了一条船。船靠岸,我兴奋地迎上去,结果从船上只走下来体育老师。体育老师挑着一副担子,他说:“其他老师不来了,让我当代表,他们把你上大学的用品准备好了,让你好好学习。”我打开担子,里面有一个脸盆,一只水桶,一只热水瓶,一个铝饭盒,一大摞崭新的写字本,一大把圆珠笔,还有两本字典:一本是《新华字典》,一本是《英汉小词典》。四十年了,字典我还保留着,就放在我办公室。有它们陪伴,如师在旁,师恩难忘。